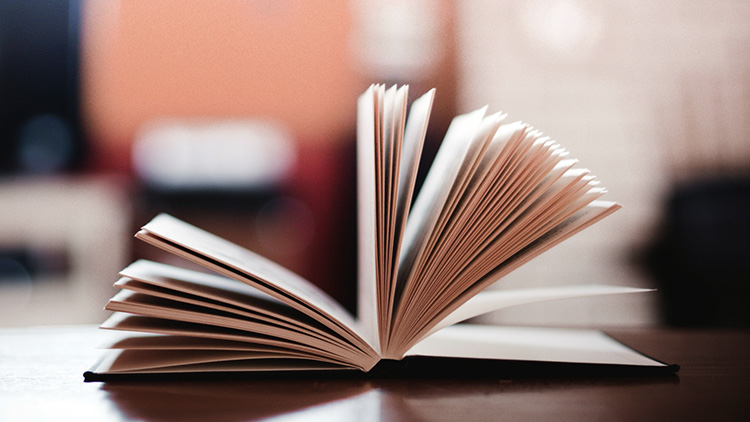编者按
“特别是对于西医,国人的信仰力尤为不足。如此一来,在医病双方之间,特别是西医与国人之间,明显地形成了不易调和的紧张与矛盾,从而也为医病纠纷的产生带来了重要影响。”作者在文中撷取了较为典型的诉讼案件来论说西医东传和现代医疗模式的建构给医病纠纷的发生带来的影响。本文出自《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有删节。马金生,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副研究员。
传统观念与现代医疗模式的紧张
在传统中医文化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国人特别是对身体越发关注的城市人群,无疑是积极推行现代医疗模式的西医师所不易应对的。在传统中医文化的影响下,国人渐渐形成了一系列用以感知和表达自身状态的概念和语言。诸如上火、体虚、受寒等疾病概念,时常被国人挂在嘴边用来描述自身的不适感觉。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在延续。病人的这些不可名状的“身体感觉”,是很难用现代科学通过数据加以精确量化与清晰界定的。换句话说,受传统医学影响下的国人对于疾病和身体的认知,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西医知识是凿枘不通的。然而,正是这套与西方医学彼此相异的身体观念与医疗知识,却在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深受此种影响的病人与标榜科学的现代西医师遭遇时,两者之间的紧张也就在所难免。从病人方面来看,当自己的身体感觉与疾病认知遭到医生的质疑或被视如敝屣的时候,那种与医生的疏离和不信任感可能便会油然而生。同样,当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根本不识现代医学为何物的病人时,民国时期西医的那份不满与无奈也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20年代末,曾经留洋日本、后回上海行医的西医余云岫,便曾对中国病人在诊病过程中的“自以为是”颇多抱怨。
余悬壶沪上,十年于兹矣。遇有善怒多倦不眠虚怯之病人,彼必先自述曰:我肝火也。若为之匡其谬误曰:肝无火也。真肝之病,不如是也,此乃精神衰弱也。则漠然不应,虽为之详细解说,以至舌敝唇焦,又切实疑信参半。若直应之曰:唯唯,此诚肝火也。则如土委地,欢喜欣受而去者,比比然也。如之何医者不乐行此耶?是以今世新医,亦有只按脉处方者矣,以为对付不彻底之社会,如实而已足也。
同样,在1930年代初期,一位显然颇为认可现代医疗模式的医师,结合自身的日常诊疗经历,对国人的医疗观念进行过非常形象地记录。个中颇体现着医病双方各自所秉持的一套迥然有异的医学知识体系,在彼此遭遇之时所产生的内在张力。他写道:
对于来就医的病人,照例我是要先问他:“某先生,您是怎么呢?”或是说:“您是哪里不舒服呢?”我总也不问:“您得的甚么病?”但是许多的病人却回答说:“大夫,我有胃病。”有的说:“我有肺病。”有的说:“我受了湿气。”有的说:“我上焦有火啊。”有的说:“我这病是由气上得的,我这人肝火太旺。”……前几天有一位朋友来求我给他的母亲看一看病,他说:“家母这病横竖是由气上得的。”病状是发热,腹痛,恶心,水泄,不思饮食,四肢酸痛。我诊视以后就安慰病人几句话说:“我想您这病就是平常的痢疾,不要紧的,要好好的调养。”病人却呻吟着表示反对说:“我这不是痢疾。”我心里说:“她看不起我么?不信任我么?”然而,她确是以为她自己比我这个医生更明白她自己的病。
“得病乱投医”虽是一句俗话,实际上这种现象,也真不少,就是知识阶级,也常免不了。至于愚夫愚妇,对于处治病人,更根本不懂。谈到卫生,他们更闻所未闻了。所以他们一遇有病人发生,必先求神问卜,试偏方,或到药店药房问病买药。亲戚说甲种的药有效,就吃点甲种药;邻居说乙种药好,就又吃乙种药。像这样处治病人,病哪能好呢?等到第三步才去求医,但是求医又不去请正当的医家,专好去找那些近于神怪的江湖骗子,不但病没有治好,反耽误了治疗的时间。金钱损失,还是另一个问题。等到觉悟了之后,再送入医院,可是已经病入膏肓,大半已难医治有效了。因为这种卫生常识缺乏而致死亡的,实不在少数;又因乱投医的结果,受社会上江湖医生的诈骗,也是常有所闻。尤其是热闹的都市,真是无奇不有。……
西医的东传,不仅带来了迥异于中医的新式医疗模式,而且在诊断与操作上也为国人带来了许多新奇的医疗器械。新式器械的应用,在使国人大开眼界、感叹其奏效迅捷的同时,亦不免令国人多少抱持恐惧与拒斥之心。西医动辄用刀切割身体或以针管将药液注射的行为,毕竟与国人传统的身体认知理念相左。 ……
再以手术为例,范守渊便曾指出,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行医的医师们“时常会得碰到害怕开刀的病家”。
这一类病家,因为对于这“开刀”二字,有了先入之见的害怕心理,于是自己或家族一旦遇到有需用于开刀的毛病,他们总想尽种种方法来反对:对于年纪轻的小孩子,不消说,拿“年纪太轻吃勿消!”的理由来反对;岁数太大的老人家,又拿“年龄太大不相宜!”的理由来抵拒;不大不小的中年人,说不定,又会想出百般反对的理由,以达到不要开刀的目的。
对于病人害怕开刀这一现象,范守渊认为,这主要与开刀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及其对身体造成的疼痛息息相关。
他们所以害怕开刀的原因,揣摩起来,不外于这么二点:1.视“开刀”这项手术疗法,是一种很危险,而非安全的办法;2.以“开刀”为十分痛楚,而非王道的治疗方法。……
西医是“灵不灵当场出彩”的,他会在你大腿上刺一针,叫你如杀猪一般的叫起来;你脑袋觉得烫,他就给你两个冰袋;你身子怕冷,他就替你生火;肚里难过吃药水,也许生个热疖会挖掉一块肉。说者谓这样似乎太欠忠厚,然而“死去”“活来”倒也不失为“直截了当”。……
现代医疗模式的践行与医病纠纷的发生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然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医病互动的大体特征进行一初步的概括与总结。一方面,西医与部分新式中医基于新式的医业伦理,试图对国人重新进行规训与形塑;另一方面,国人特别是在大都市中越来越关注自身身体的人们,由于受到传统医疗文化的影响,依然对医生抱持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对于西医,国人的信仰力尤为不足。如此一来,在医病双方之间,特别是西医与国人之间,明显地形成了不易调和的紧张与矛盾,从而也为医病纠纷的产生带来了重要影响。也便基于此,雷祥麟指出,正是由于医病双方在建构新型的医病模式中的相互摸索和彼此冲突,“造成了三十年代盛产的医讼”。应当说,这种识见是非常到位的。
为了较为清晰地考察现代医疗模式的建构为医病纠纷的发生所带来的影响,我从1930年代发生的医讼案件中,撷取了几则较为典型的诉讼案件进行分析论说,希望能够具体地呈现出医病之间的这种紧张与冲突。
1因对医疗器械的恐惧而产生的纠纷
对冰囊的疑惧与排斥,在民国时期的一般民众中确实形成了一个“准共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诉讼案中,但凡医师曾用过冰囊,一般均会被作为控诉理由。比如,俞松筠医师讼案,便是如此。在这起讼案中,病家田鹤鸣之妻在上海中德产科医院生育后,出现乳胀的症状。于是,俞松筠乃用冰袋冰敷产妇乳房用以消胀。后来,产妇接连腹泻,最终身死。于是,田鹤鸣不禁将冰袋的使用与腹泻联系起来,“产妇最忌受寒,被告更不应令产妇于睡眠中用冰袋,且腹泻随冰袋而发生,足见冰袋可使产妇受寒,并减低其抵抗力而利痢菌之繁殖”。
除去冰囊之外,国人对注射器、手术刀具等也有很大的排斥心理。因此,当用注射器注射、用刀具切割身体而终使病人于不救时,部分病人家属也会据此而作为兴讼的理由。这在邓青山医师讼案中,便有着集中体现。彭武扬之妻胡尔欣因咽喉痛,前往九江牯岭医院求诊。医师邓青山认为病人所患为白喉,乃以医院尚存过期不久的血清为病者注射于手臂。然而,就在注射后不久,病人病情忽然大变,“两手震动,气喘,遍发红点”。邓医师一见不妙,立即进行抢救,“持病者两手上下摇动,以助呼吸”,复“将病人注射处,用刀划开,用两手挤出黑血两点”,“见病者呼吸更微,乃向病者胸膛复打一针”。可惜,这些举措都未能见效。病人最终身死。从病人注射血清后的反应来看,应属于对血清的过敏不适应症状。而邓医师的抢救方式,在谙熟西医知识的人来说,可能也不会感到讶异。但在胡氏的家属看来,显然不能接受。于是,彭武扬以邓青山图利,“复加残忍行为”而致病人于死为由,将邓青山医师控告于九江地方法院。
再来看一则案例。这一讼案发生在1948年12月2日。上海市民张洪源8岁的儿子张二毛中午放学回家,在路过华兴路时,不幸被谢夏氏用热水瓶烫伤背部,被北站警官孙菊林紧急送往西藏北路上海济民医院医治。在济民医院,经梅姓医师和俞姓医师为张二毛检查伤势后,由俞医生为伤者“注射一药水针”。孰料,在打过针后,张二毛旋即“闭口不能言语,面目及口舌发白,全体抖动,闭目晕沉,不省人事,疼痛失去知觉”。第二天,张二毛被送到仁济医院求诊,“口吐黄血水甚多,未及治疗,即告死亡”。张洪源见儿子惨死,便将谢夏氏告上法庭。有意思的是,张洪源后来又将梅、俞二位医师也一同告上了法庭。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与张洪源的对答,充分体现出了张洪源对于儿子之死的怀疑以及对两位医师的气愤。
(检察官)问:你儿子被烫死了,不是已经起诉了吗? (张洪源)答:是的。 问:你怎么又告谁了? 答:告医生等打针后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问:你现在是何意思? 答:我的儿子不明不白的死了,我要伸冤。 问:你认识字吗? 答:我仅会写我自己的名字。 问:关于谢夏氏部分已经起诉了,你还告他吗? 答:我现在告两个医生。 问:你告医生何事? 答:医生打针后就不能开口,一句话也不说就死了。是俞医生叫看护打的针。 问:你因何告俞医生呢? 答:我见儿子死了在那里哭,梅医生说哭也没用,你去告我好了,因此才告他。 问:你告医生何罪? 答:针打多了。……
国人对器械的疑惧,还表现在如若病人不治后,病人家属会结合病状形成某种联想或想象,并据以作为控诉医师的理由。这在当时的讼案中亦为数不少。如在沈克非医师讼案中,病人陈允之因患急性盲肠炎在南京中央医院割治身死。关于死因,院方认为“酷似肺动脉栓塞”。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起诉主治医师沈克非的理由有两条,一为对死者施双重麻醉而侵害心脏提出质疑;另一条理由则为,术后缝结肠部时,“未将血块或脂肪拣净,以致血块由割口入血液,将血管栓塞”。
第二条理由的提出,颇为有趣。因为从医理上讲,这显然不能成立。但病家却以此举控,明显是以“栓塞”而“想象”出来的结果。由于对西医的不了解,以至检察官都确信不疑。另外,在俞松筠医师讼案中,也有一条理由与此相类。那就是田鹤鸣之妻因产后便秘,俞松筠为其用皮带灌肠。而此后,产妇腹泻不止。于是,田鹤鸣认为,显系“灌肠之皮带,染有病菌灌入肠中所致”。
2因医疗协议的模糊认识而产生的纠纷
医疗协议书的使用,是现代西医的一个重要特征。大量事例表明,近现代国人在医疗协议接受上,内心也是颇为复杂的。从这一时期的医疗讼案来看,但凡涉讼的病家,多数对医疗协议书的签订持有不同程度的抵触心理。比如,在葛成慧、朱昌亚两医师讼案中,原告沈文达在《刑事自诉状》中,对于医病双方的签字是这样认识的。
彼等深知蹉跎再四,挽救已迟,深恐庸医杀人,论法应负全责,为诿卸其怠忽业务之罪,乘自诉人惊惶失措之际,迫签生死各由天命字样,以自掩其责。……庸医徒知法螺,对案务完全怠忽,以至于死。且医院纯以科学治病,而乃责人签立生死由天之据,尤属荒谬绝伦。其毫无医学常识,误人性命,可为明证。
从沈文达的《刑事自诉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医疗协议的签订,沈文达认为是“尤属荒谬绝伦”的事,完全持否定态度。同样,在葛成慧医师所遭遇的另一起医疗讼案中,当病患家属李石林对尚贤堂妇孺医院的诊疗完全失去信心后,要求将妻子从医院中迁回家中医治。出于对医院权益的考虑,妇孺医院要求李石林必须先签订自愿出院书,李石林认为此举显然是院方日后为了推卸责任,因此十分愤怒。
自诉人知病势凶险,留院无益,决拟迁回家中医治,求最后之一线希望,而该医院乘机迫令在铅字印就之自愿出院书上签名,为日后图卸责任之计,可恶尤极。
再来看一下江明医师讼案。在这起讼案之中,14岁的贫农之子余年福患咽鼻部纤维瘤,“大如鹅卵”。在其父余以海的陪同下,送往南昌医院求治。江明医师在为病患诊视后,认为只有将瘤割除,否则终将身死。在征得病家的同意后,按照南昌医院的规则,病家需具结觅保。由于余以海不识字,载有“倘有不测,各安天命,与贵院及各医生毫无干涉”字样的甘结,只得由余年福的母舅刘静山签署,病人余年福在甘结上按了手押。
江明医师的手术并不顺利,余年福在实施麻药的过程中身死。签订甘结一事,成为医病双方争论的焦点。医院方认为病者在入院之初即已签订甘结,在医师无医疗过失的情况下身死,自然与医院和医师没有干系。然而,即使医院方面出具了当初入院时所签押的甘结,但余以海却矢口否认有签押甘结之事,并声言江明医师也从未向其说起过“割治危险之厉害”,“他如说危险,当然不肯割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南昌地方法院认为,尽管在入院时签有甘结,但仍不能免除医师治毙病人的责任,一审判决江明医师有罪。
颇为有趣的是,尽管民国时期的国人对医疗协议书多持抵触心理,但在有些情况下,如不签订医疗协议书往往也会被病家利用,并成为引发诉讼的理由。在《医病签字之检讨》一文中,西医瞿绍衡便曾指出,只有医师在实施危险性的诊治(如手术)时,出于慎重才会采取签订协议书。目的是万一发生不测时,“免病家之误会,或听信旁人之怂恿,而滋枝节”。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若医师并无医疗过失,即便医病双方因故未在之前签字,“亦不能遽责以手续不完,便令负何责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世人不察,有以事发不得签字引为口实而起无谓之纠纷者”。
由此一来,许多医师被迫卷入医讼之中,不但名誉受损,一些“忠厚畏事之医者”不得不委曲求全,“赔偿来缠者以若干之愿”。 ……
关于医师在症起仓促时的顾虑,瞿绍衡讲述了两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例。 一则发生在1937年,一男子陪同产妇入住医院待产。男子在签署住院保单并交纳住院费用后离去。不想产妇夜间“剧痛,至午夜忽起变化,势非施行手术不可”。瞿绍衡急忙让院役按照保单上的地址去找签保单的男子,然而却并无此人。当时产妇“时势益危”,瞿绍衡百般无奈下只得在街上叫来一名安南巡捕,在后者同意做证人的前提下为产妇实施了手术。瞿绍衡所讲述的另一则事例,发生在1937年12月的一个深夜。一“其状非常狼狈”的妇人扣门求诊,当其进门后“呜呜不能言,腹痛不能步,腰弯不能支”。待将妇人抬入产室,褪去衣裤时才发现婴儿已“露顶矣”。这一突发事件,着实让瞿绍衡颇费踌躇。在良心的驱使下,瞿绍衡最后还是为产妇进行了接生。尽管产妇顺利产下婴儿,但也着实令瞿绍衡异常担心,“倘或不测,早步杭州某医师之后尘矣”。
从瞿绍衡的文章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当时的国人对于医疗协议书的认识,的确不是很清晰。在医师看来,本来用以表现稳妥慎重的行为,最后竟然会成为病人家属举控的理由,难免让人心寒。不过,从病人家属的角度来看,协议的签订,多是在遇有危险的诊疗之时。病人一旦发生变故或者身死,病人家属心中本就无法释然。因此,对协议书的再三强调,更会让病人家属产生医师在推卸责任的看法。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医的在华传播与中国本土传统产生了诸多疏离和紧张。而通过对这些疏离与紧张的深入探讨,往往会让人们别有收获。如上所述,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医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已然站稳脚跟。中医界通过积极革新也取得不小进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等大城市的名医也开始树立起了专业权威。西医以及新中医对现代医疗模式的强调,显然让依然抱持传统医疗观念的国人不易接受,进而给现实中的医病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就在医病双方围绕现代医疗模式的磨合中,摩擦与龃龉也在所难免。特别是对于西医来说,医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为明显。
通过对西医诉讼档案文本的解读,可以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医医讼的“盛产”,确实与当时西医所大力建构的现代医疗模式以及对新式医疗器械的使用与中国的本土传统存有很大张力有关。面对西医基于西方医学伦理而展开的对国人的规训,在本土传统的影响下,国人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形式多样的“反抗”,表达了自身对西医的部分看法和态度。医讼案中病人及其家属的发声,便集中体现了国人对西医的一般感受与想法。当对疗效不满后,病家的疑虑、焦灼、想象、恐惧,诸多情感交错杂陈,在诉讼状中得到了强烈的爆发。当然,事实证明,这些“反抗”最后都在拥有强势话语权的西医面前以失败告终。本土的医疗传统,最终让位于西医的专业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说,西医讼案中医病之间的这些较量,也便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角力的一个缩影。